

出品 | 虎嗅青年文化组
作者 | 木子童
编辑、制图丨渣渣郡
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“那個NG”(ID:huxiu4youth)。在这里,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、故事和态度。
《周处除三害》俨然已上神坛。
已经很久没有一部中国台湾电影,能在大陆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:上映不过5天,票房已经过亿,而且豆瓣评分一度高达8.4分。
虽然这两天评分已经回落至8.2,但这依然是今年所有华语片中的最高分,社媒激情澎湃的赞美无限拉高了观影预期,有观众评论:“好久没觉得在电影院观影是件这么幸福的事情了。”
然而带着高预设走进影院,通常都是不幸的开端:影片的确是好看的,但距离真正封神,似乎还差那么一口气。


讲坏话之前,先把好的说完。
首先必须肯定的是,《周处除三害》是一部水准以上的犯罪动作片。不论是颇有新意的剧情、还是流畅丝滑的打戏,既有惊喜,也见演技。
我们之后的所有“吹毛求疵”,都将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:这是一部值得被要求更多的作品。
【以下内容涉及剧透,请谨慎阅读】

观看《周处除三害》,最直观的感觉就是爽。即使不带脑子,也能看个尽兴。
简单来说,这就是个通缉榜榜三大哥决定干掉榜一榜二的黑道爽杀公路电影。
整个故事如同直道上疾驰的赛车,呜地一声起步,随后油门到底,越飙越飞:
阮经天饰演的黑道杀手陈桂林,敢在黑道大佬葬礼上枪杀继任大佬的狠人。在逃四年,一朝发现身患绝症、时日无多,在黑道医生劝说下动了自首的念头。

但到了警局他发现,竟然没人认得自己,那些曾自以为惊天动地的“大事”,早已被人遗忘。就连斑驳泛黄的通缉榜上,他也只是区区榜三。
陈桂林不怕死,但怕默默无闻地死,他说:“我不是怕死啊,我是怕死了都没人记得”。

于是当场决定干掉榜一榜二,在死前求一场轰轰烈烈的盛名。
这一路,神挡杀神,佛挡杀佛。没有人能在物理层面阻挡他,也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能让他的屠刀变钝。
恶贯满盈的坏人要杀,为虎作伥的喽啰要杀,手无寸铁但愚信不返的邪教徒也要杀。只要是陈桂林相信该死之人,统统被“立即执行”。
一路砍瓜切菜,血浆四溢,荡涤环宇、诸邪避易。最后果然得了天大的名声,顺手解救了不少受害者,本人也以杀证道,浪子回头。
传统黑道片喜欢强调道义、克制与悔过,而《周处除三害》完全不在乎,它以一个脱离于世俗的边缘人主角,完成了秩序之外纯然的快意恩仇。
仅仅理解到这个层面,是不需要任何思考的:片中有拳拳到肉的丝滑打戏,有柔弱无助的香艳裸女,也有Cult片属性拉满的洗脑邪教,可以一路裹挟感官与主角一同狂飙。

而如果带了脑子走进影院,将得到更多。
你会发现,导演黄精甫果然惯爱象征与隐喻,整部影片被密集的象征符号镶嵌得如同一本解谜书。
片名便是一把钥匙,《周处除三害》引自《晋书》和《世说新语》所载典故:
相传魏晋人周处年少时自恃武艺高强,于是横行乡里,和附近肆虐的白额虎、水中蛟被并称“三害”。有人怂恿周处去干掉虎、蛟,希望三害相斗,两败俱伤。周处欣然前往,缠斗三日,斩杀虎、蛟。结果回乡之时,发现乡亲们以为他已经死了,正在弹冠相庆。周处于是顿悟自己为人所厌,从此幡然悔悟,改过自新,终成一代名将。
由周处而观陈桂林,暴力外衣包裹下的,实则是一段自我发现的故事。
更多细节,草蛇灰线,伏脉千里。
黑道医生陈贵卿去医院领胸片时,诊室门外医生名牌上书“庄依仁”,看似是接诊医生的名字,实则暗示贵卿的身份,“装作医生的人”。

陈桂林回家开门前,从门轴上取下一颗花生米,抛进嘴中吃掉。这既是表现一名通缉犯的反侦察意识,也是枪决的隐喻。玩笑话里,“吃花生米”便是“吃枪子”。

如果想要细细咂摸,那么《周处》也可以被咂摸得有滋有味。
能够看出,《周处》在大陆取得成功并非偶然。然而,这样一部好看的片子,是否就因此够格封神呢?
对比同样聚焦通缉犯的《烈日灼心》,亦或是阮经天另一部名作《艋钾》,它似乎又差了那么一口气。

不上不下,是《周处》最大的遗憾。全片始终在一种极端的氛围下推进,但在最后,却似乎少了一股力道,缺了一种癫狂,于是最终没能抵达某种令人哑然的极致震撼。
不是因为导演没有表达,而是表达太多。正如朋友在影片结束30分钟后的发问:“它到底想讲什么?”
是浪子回头金不换?还是善恶报应老天在看?是邪教真可怕?还是王净真好看?似乎都是,又似乎都不是,庞杂的主题交织在134分钟影片里,时而相得益彰,时而互相矛盾。
因此试图在《周处》中深挖意义,就会像在儿童泳池潜水,深吸气一猛子扎下去,发现一蹬腿就摸到了池底。

以主角陈桂林的行为逻辑为例,在影片的绝大部分它都十分连贯,但结尾却有了突兀的转变。
陈桂林除三害的初衷很简单,为了扬名,为了死后有人记得。杀人是他扬名的手段,因此他从不为开枪而后悔,即便枪下亡魂中,很多人可能在法律层面上罪不至死。
被警察逮捕时,记者问他:“你后悔吗?”
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,而是无比满足地举起双手,兴高采烈地大声重复:“我叫陈桂林!陈!桂!林!”

他为以杀证道的自己感到欣喜、骄傲和安宁。
然而这样的他,临刑前却突然表露出了惭愧与悔意,遗言道:“我对不起大家,对不起社会。”
这样一个自始至终就未曾进入过主流社会秩序的存在,突然表现出愧悔不仅令人错愕,更令人困惑:这份歉意究竟指向哪里?
如果说陈桂林认为毕生所杀都是当杀之人,那么何来对不起?
如果陈桂林最后幡然悔悟,愧悔杀孽,那么他凭什么以如此宁静喜乐的神情迎接终末?


前后矛盾的行为逻辑,最终让这个人物成了一个不可知也不可解的谜团,影片用两个小时堆叠起来的某种神性,也就此回归庸常。
不止一个角色如此:
警察陈灰,早年间追捕陈桂林时被打瞎右眼,因此多年来不死不休地追踪陈桂林,以命相搏。然而最后陈桂林自首时,陈灰突然与陈桂林熟络起来,如同老友般温柔以待。
这或许会被解读为某种对于“义警”的激赏,但对于一个恪守程序正义多年的刑警来说,这种毫无交代的转变不可谓不突兀。

于是任何试图解读影片的尝试,都在彼此矛盾的动机与逻辑中陷入困境,在找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前就已迷失。
其实再多了解一点背景信息,这些别扭之处多少可以解释。
譬如陈桂林为何在行刑前要说,“我对不起大家,对不起社会”?
这大抵是因为,陈桂林并非凭空建立的人物,而是有其原型。原型便是台湾著名杀手刘焕荣。
刘焕荣,绰号“神经刘”、“冷面杀手”,是“竹联帮”忠堂执事,因犯下多起枪机杀人案而被通缉逃亡。虽是杀手,刘焕荣却颇有侠气,一生绝大多数时候,只杀黑道中人。平日里更是仗义疏财,曾经抢劫赌场,只为协助一家破烂孤儿院重建。
伏案后,刘焕荣改过自新,在狱中多次发起捐款,匿名支援贫苦人家,并把狱中书画拍卖所得捐给妇女救援基金。
“我对不起大家,对不起社会”正是他临刑前所留遗言。

如果将陈桂林带入刘焕荣的身份背景,他的行为逻辑便好理解了许多。刘焕荣虽然脱离于社会秩序之外,但依旧向往回归秩序。
他的脱轨与其说是天生如此,不如说是被逼无奈。17岁时,刘焕荣本想毕业后报考军校,但因为年少时留下过案底,被拒之门外。
紧接着,台湾发布《检肃流氓条例》,警察背上抓流氓的KPI,完不成时,便会找刘焕荣这个有过“打伤警察”前科的人来充数。
一来二去,刘焕荣欲走正道而不能,只得在邪道上走到黑。
陈桂林道歉的一种合理解释是,他本就不是一个仅仅沉醉于杀人扬名的愉悦犯,而是始终在渴望回归“常态”。

只不过此时,导演给观众的又太少了。
既没有提及陈桂林之所以成为陈桂林的经历,也没有表现过陈桂林除了“求名”之外的其他欲望。他仿佛一个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,没有来历,没有人欲,也没有去向。
兴许导演是默认了,刘焕荣的故事家喻户晓,早已不需要多着笔墨。
但台湾之外的观众,显然需要创作者多一些用心。

另一方面,成也隐喻,败也隐喻,正是过量的隐喻与象征,最终暴露了《周处》立意的模糊。
如果说契科夫的戏剧里,在第一幕里出现一把枪,第三幕枪一定要响。
那么《周处》中,很多把“枪”都默默哑火了。
它们或许不那么引人注目,但也实打实让一些隐秘的期待落空。
在邪教暴乱的场景中,镜头一次次给向邪教头子的女教徒情人,她站在祭坛的最高位,充满神性地漠然凝视眼前的杀戮,仿佛暗示着背后还有什么更大的反转。
然而没有,什么也没有,女情人唯一的记忆点,只有唱歌真好听。

再如影片英文名“The Pig, the Snake, and the Pigeon”,猪、蛇和鸽子,在佛教中被视为三毒,分别对应“痴、嗔、贪”三害。
陈桂林有一只奶奶给的小猪手表,他是痴迷于名的“痴”。
榜二大哥香港仔有一条细蛇文身,他是凶狠残暴的“嗔”。
榜一大哥林禄和背负文身鸽子,他是贪得无厌的“贪”。



看似让“除三害”的主题又多了一层戒除贪嗔痴的深意,但影片中并没能抽出笔墨对贪嗔痴进行思辨,贪嗔痴的符号也没能辅助推进剧情、深化逻辑。
陈桂林之所以要香港仔与林禄和去死,并非因为对方嗔怒或贪婪,只是因为对方排在通缉榜前面。
贪嗔痴的象征有或没有,对影片推进都不打紧。
与其说这是一种“高明的表达”,不如说更像一种“高明的包装”。
它不一定真的高级,但能让影片看起来足够意味深长。
而这一支支没能扣响的“装饰枪”,便让《周处》差一口气的窘境越发显眼,似乎导演有意收敛,把最攒劲儿的东西藏了藏。

若是讲浪子回头,那么浪子好似无根之木。若是讲依循本我、快意恩仇,那么最后对社会规训的承认就是一种狂气的折损。
最终什么都想说一些,又什么都没点透。
实际上,《周处》在台湾的票房与它差一口气的状态相当匹配,口碑上佳,却只有区区1071万元票房。
毋宁说,它在大陆市场的爆火,反而是一个异数。
《周处》大陆爆火,“尺度”功不可没,这些天,社交平台上喧嚷最盛的,莫过于《周处》的尺度。
的确,不论是性奴、邪教、集体屠杀,还是纯粹的恶人主角,都是近年大陆银幕罕见的景观。
影片宣发时也以“台湾影史极恶电影”自我标榜,大家都想去影院看看,这片儿到底有多少儿不宜。

然而观影后会发现,要说《周处》血腥暴力,对于吃过见过的观众来说,也不过尔尔。
陈桂林与香港仔缠斗时的啃嘴杀,《汉尼拔》里见过。
教堂里对教徒的利落枪决,《王牌特工》里见过。
血腥战斗与肢体残损,比不过《红海行动》,死刑的实拍,不及《烈日灼心》中邓超的直给。

真正的尺度还是在剧情之中:一个极恶之人,通过极恶的行动也能照见真我,成就某种神性。
这一过程的绝大部分时候,无关悔过,无关秩序,有的只是一个怪人对自我意义的追寻。
这种癫狂的过程,就像把普通人平日里对恶人最咬牙切齿地惩罚幻想变成现实,让司法之外的快意恩仇获得准许。
而这明显有些邪性的路子,才是大陆影视中真正的稀罕。
影片最后,用陈桂林的改邪归正完成了社会秩序对“任侠之人”的招安,也让“尺度”回归能够容忍的底线。这当然是正确的,合理的,因为故事原型正是如此。
但对于一部从头癫到尾的影片来说,这无疑也是一种减损,狠勒一把的缰绳,让即将化为长啸的狂气变成差一口气。
最终,影片在行刑警察的一声枪响中滑入平凡的世界,徒留一张空茫的脸。
太过确定的结局,同时泯灭掉更多咀嚼与想象的空间。

相比于此,影片中更多略有神秘学色彩的桥段,反而更加迷人。
第一次自首前,陈桂林掷筊求问关帝爷,是否该去自首,关帝爷连续9次给出一阴一阳的圣杯——该。
本来无意自首,希望借天意以逃避的陈桂林,在投出一次次圣杯中满头大汗、浑身颤抖,最终认了天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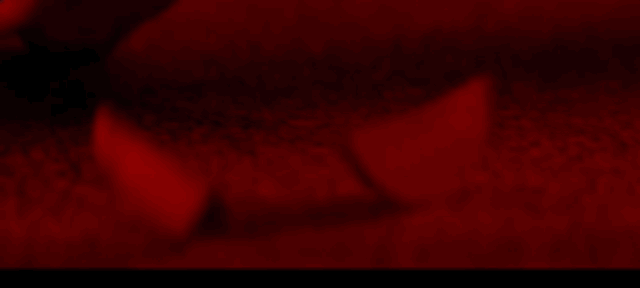
而他在对决邪教头子林禄和的终极决战里,再次将一切交给“天意”,只不过这一次代表天意的神明是他自己。
他枪指林禄和说:“如果我枪里接下来9发子弹都卡弹,我走。如果没有,那就是天意,那就是上天惩罚你玩弄苍生。”
第一枪,卡弹,第二枪,卡弹,就连林禄和本人都忍不住露出一丝丝我是否真的受命于天的侥幸,然而第三枪,枪响了,林禄和应声而倒,一命归西。

自古天意高难问,但此时天意似乎又与善恶果报产生了某种关联。
这种带有宗教与宿命性的空枪设定,并非黄精甫第一次用在自己作品之中,在前作《复仇者之死》,他也使用过同样的设定。
于是思及于此,忍不住便会有些遗憾,结局的枪决,会不会有某种更具解读性的表达方式,能够替《周处》顶上成神路上的最后一口仙气?
比如,连续9次卡弹之后的一次枪声?

 支付宝扫一扫
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