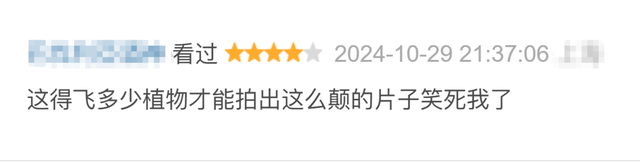《某种物质》(The Substance),这部来自法国女导演科拉莉·法尔雅(Coralie Fargeat)的“身体恐怖片”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展映时,便无疑成为了今年最受瞩目的影片之一。正如导演本人所承认的,在影片充分致敬了大量前人杰作,包括但不限:希区柯克《惊魂记》(Psycho)、斯坦利·库布里克《闪灵》(The Shining)与《2001:太空漫游》(2001: A Space Odyssey)、布莱恩·德·帕尔玛《魔女嘉莉》(Carrie)、大卫·林奇《象人》(The Elephant Man),还有大卫·柯南伯格、约翰·卡朋特等等。
有意思的是,法尔雅非常有意识地借助了男性导演的恐怖/邪典电影遗产,来为影片增添性别议题上的争议(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影片评价两极分化),关于一个昔日好莱坞女星因“服美役”而不断自我剥夺的悲剧故事,观众却能够在其中读出“厌女”与“女权”的双重含义。
下面,我们将沿着邪典电影的历史,来探究这样的两极的价值是怎么共存在同一部影片中的?

《某种物质》
首先,如果用“厌女”与否去衡量恐怖电影,那你将会发现,对女性身体的剥削和戕害,一直是恐怖片的传统看点。正如希区柯克所说的那样——所谓电影,就是“折磨她们!”
那些在恐怖片中的经典受虐女性形象,恐怕怎么数都数不完: 她们是《驱魔人》(The Exorcist)中被撒旦附身的小女孩,是希区 柯克电影里的金发女郎,是铅黄电影里的女杀手,是《月光光心慌慌》(Halloween)、《德州电锯杀人狂》(The Texas Chain Saw Massacre)中传来的一阵阵女人尖叫……

《月光光心慌慌》
我们也可以沿着七十年代劳拉·穆尔维《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》(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)一文所阐释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,对恐怖片中女性形象的使用进行分析,那个如今已经或多或少被滥用的“男性凝视”(male gaze)有着它精神分析学本源的含义——摄影机的凝视、男性角色的凝视,以及男性观众的凝视所构成的三位一体。

《德州电锯杀人狂》
在此基础上很容易得到的一个结论是,几乎所有恐怖/惊悚片都该是“厌女”的、男凝的,因为它们共同上演男性施虐与女性受虐。
但凝视是既充满欲望,又充满恐惧地观看,所谓“男凝”还隐藏着经典好莱坞电影中的男性阉割焦虑。
在六十、七十年代盛行的意大利铅黄电影,以及后续在美国流行起来的血浆片(splatter films)和砍杀片(slasher films)中,在它们邪典的视觉风格下,还隐藏着另一种叙事:女性夺势,以及对女性夺势的污名。这与当时意大利的离婚合法化、战后女性进入社会工作,以及欧美社会的青年反文化运动、女性平权运动、性解放运动相关联。
例如,意大利铅黄电影(giallo)大师达里奥·阿基多的影片,就向我们展现了男权失序的焦虑。《夜深血红》(Profondo rosso)中刻画了几近无能的男警探,恶魔般的母亲,以及因父爱缺失而后天形成的同性恋儿子。

《血与黑蕾丝》
在美国,堕胎合法化,避孕药被发明了出来……说这一时期的恐怖/惊悚片呈现了男性的性恐惧与性焦虑也非言过其实:《驱魔人》中被撒旦附体的小女孩成为一个绝佳喻体,性解放与平权思想的魔鬼玷污了贞洁,扼杀了童真。在《月光光心慌慌》与《德州电锯杀人狂》中,放浪的女性总是惨死,她们甚至往往死于与男性做爱之后(这几乎成为一种套路),而贞洁的女性总能逃出生天,尽管在逃脱之前杀人狂对她们实行了追杀与虐待……

《驱魔人》
但,邪典电影本身就是一场关于观众解读权的争夺,男性导演的恐怖/邪典文化,在后来的女性/性少数观众解读中,逐渐被赋予另类色彩。观众解读权的争夺,就是话语权的争夺。

“回视凝视”,夺回解读
穆尔维理论以及其所代表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电影批评,有着同样的缺陷:当我们仅仅用“男性凝视”去理解恐怖/惊悚片的时候,将会陷在文本分析的单一限制,和僵化的阐释路径里,而忽略了观众本身多样的观看体验。
也难怪劳拉·穆尔维在近期接受采访时,对她本人近五十年前的阐释作出了这样的回应:她后来“逐渐将好莱坞视为对父权心理进行批判的丰富素材来源。”(I came to see Hollywood as a rich source of material for critique of the patriarchal psyche.)
穆尔维留给我们的遗产是,当她指出经典好莱坞影像所潜藏的男权机制之后,便将性别这一观念深深扎进了影像的制作与观看的实践中,她进而试图告诉我们,在父权讲述的故事之外,还有一大片其无法触及的空间。
而在1984年,琳达·威廉姆斯就在穆尔维的阐释的基础上,写就了《当妇女凝视时》(When the Woman Looks)。其中指出——恐怖片是让女性可以“回视凝视”的影像。

《分手的决心》
她认为,尽管“怪物”在恐怖片中威胁了女性的身体,但女性与“怪物”的命运又是息息相关的,两者都被放逐在了父权结构之外,她们本身就代表着对父权制的威胁。而作为观众的我们,不得不观看女性/怪物的“回视凝视”——观众同样可以认同于《驱魔人》中遭到撒旦附身的小女孩,当我们认同于她时,朝向神父的亵渎,就变成反文化的力量,践踏着主流社会的世俗规则。

《本能》
但威廉姆斯同样也承认到,女性因挪用“凝视”而受到惩罚,最终还是会回到男权秩序当中。无论我们事实上认同于施虐方还是受虐方,传统恐怖/惊悚片总是还要驱逐主流/男性观众的心理恐惧。站在电影类型策略本身的逻辑上,这是无可厚非的,因为它最终诉诸的还是主流观众的票房。
而这样“回视凝视”的观众解读策略,到底是一种“精神胜利法”式的无能为力的自我赋权,还是说,恐怖/惊悚类型本身就是包含着“双重认同机制”的影像编码?
这涉及一个亚文化的观众解读策略的问题。在恐怖/惊悚片中,观众,尤其是女性观众究竟是认同于施虐的男性,还是认同于受虐的女性,而当其认同于受虐的女性时,获得的是受虐的快感,还是作为受害者的复仇愤怒。而如果是受虐的快感,“到底何种界限会超过可以承受的范围,因过于荒谬而难以称其为快感?”
对此,我们还可以延伸到这样一个问题来:近年来,在伪现实主义国产电影中,对女性进行剥削的“虐女”场景,与这种恐怖邪典文化脉络下的观众施虐/受虐快感究竟又是不是一回事?

《涉过愤怒的海》
差别就在于“现实主义”本身,恐怖/惊悚毕竟不诉诸任何现实议题,本身是商业的影像消费逻辑,但当触及现实议题时,施虐/受虐场景提供的是现实的奇观化功能,将观众目光凝聚在“真实”的受害者身上,本质上是“现实罪行该不该被奇观式的展示”的商业影像伦理问题。

受虐狂式的女性主义
在八年前的同一舞台戛纳电影节上,保罗·范霍文的《她》(Elle)同样进入了主竞赛名单。影片则是直击女性在施虐/受虐身份的议题,电影中的女主角米歇尔在遭受暴徒强暴后没有诉诸警方,而是自己调查罪犯,最终发现这个暴徒就是自己后来爱上邻居……

《她》
电影充分利用了室内空间来释放惊悚感官,可是说是对伍尔夫“女性要有自己的一间房间”的崭新诠释。米歇尔并没有内化男权社会的强暴羞耻/贞洁恐惧,对她来说暴行甚至是对受虐性欲的极大满足,以此便完成了男女权力关系的绝对逆转。范霍文 2021 年的《圣母》(Benedetta),同样构想了一个凌驾于父权/宗教的修女形象。

《圣母》
当然,再延伸下去,拉斯·冯·提尔的《女性瘾者》(Nymphomaniac)也同样是类似的性别权力逆转的叙事策略。他们完全拒绝了上述所说的——恐怖/惊悚片是“双重认同机制”的观念,拒绝了这种介乎模棱两可的创作实践,而构想出一个完全颠覆了性别秩序的世界,一个他们自己打造的真空空间——在这个空间里,女性能在受虐快感中获得极大满足,以至于“受虐”反而可以反转成为她们的自我赋权。
一方面,拍摄此类影片的男导演们的暴君属性也体现在此:另一种将人物剥削到极致而焕发的心理效果。但另一方面,这些因为在银幕上呈现女性裸露的身体,而被打上了“厌女”标签的男导演们,在他们激进、颠覆和挑衅的影像中,最终却迸发了一种女性主义的张力。
当然,需要指出的是,正如我们都知道,这只是作为惊悚片的前提设定,和他们作为作者电影导演(auteur)的自我风格,现实世界显然并非如此——真实的情况是,女性仍是社会中占据绝对主体的受害群体。而如果没有拒绝暴力的自由,亦不可能有追求暴力的自由。这在性暴力议题中常被男性罪犯偷换概念。

《女性瘾者》

作为邪典必然会继承的指控与自证
如果说西部片、黑帮片、歌舞片在今天差不多已偃旗息鼓,那么恐怖/惊悚片似乎还没有就此罢休的迹象,在今天,恐怖/惊悚片仍然是最有效力的类型,不论是在商业性上,还是亚文化影迷认同上。这一类型反映着主流社会的恐惧心理,只要主流社会依然有它的反面,恐怖影像就依然有它的可书写之处。
更何况,亚文化也从来不是主流文化真正的反面,而是它召唤出来的一个镜像,毕竟影片最后仍要重回主流价值(《某种物质》最终还是要杀死一个虚荣的女性,而现实的父权秩序毫发无伤),而女性“回视的凝视”最终要因挪用了凝视而招致惩罚。

《魔女嘉莉》
我们进一步会想,女性在邪典文化实践之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?邪典文化是否从一开始就是男本位的?写作了《邪典电影:一种亚文化的历史》的学者李闻思在其论文《“女性向”消费的幽灵——好莱坞的伪女性主义逻辑》中表明了女性复仇叙事内在的父权逻辑:邪典电影作为风格被简化后,披上了审美上的女性主义外衣,便可以肆无忌惮地致影像伦理于不顾,尽情展现剥削。
酷儿若是以女性身体作为抵抗父权的武器,毫无疑问会遭到女性本身的质疑。正如在《某种物质》中,伊丽莎白/苏能做到的反抗,仅仅是在片末向舞台下的观众/银幕外的观众喷洒血浆,而在影片前三分之二的过程中,我们目睹女性在男权逻辑下对美貌的热衷,和不断地自我残害,这样的结构比例,很难让人认同于最后的复仇喷血,因为这样的自我献祭本身也是无力的。
当然,我们并不是要以“是否是真正的女性主义”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部电影,只是,我们会看到当下的女性导演,在使用邪典恐怖片(毫无疑问是男导演的遗产)的时候,她在试图平衡“双重认同机制”时,自身在其中的难堪——一方面这样的邪典风格要求类型化的“凝视”与“剥削”的元素;另一方面,它放在当下的性别权力语境下,将要不出预期地落入“厌女”的指控与自证。

《某种物质》
疼痛的女性身体,衰老所带来的容貌焦虑,医美技术的成瘾性,是女性在现实所切身体验的遭遇,在电影中重现这种疼痛当然可以被理解为对女性本身的“警醒”,但也让女性再度经历(甚至十倍地、放大感官地经历)这样的心理/身体恐惧。
当坎普/酷儿、邪典的解读策略必然与现实体验相撞,前者的想象性认同便会轰然倒塌。而这种矛盾在七十年代以来的性别分离实践中已经上演过。

解读权/话语权的逆转是否只是空想?
朱利亚·迪库诺的《钛》(Titane)是一次对于赛博格/酷儿主体想象的寓言,影片继承自柯南伯格的身体恐怖片,它颠覆了所有的既定二元框架,没有陷落在任何由身份带来的道德之中(主角在变换身份前平等地虐杀男性、女同性恋、黑人……)。
Alexia 厌弃自身的女性气质(因此有观众批评影片“厌女”),女性气质为她招来了骚扰,于是她拒绝女性身份带来的利与弊,转身投入了男性集团的怀抱。但也是在女性气质的掩护下,她拥有了许多杀戮的机会,成为她的优势。可是成为了 Adrian 的 Alexia 没有力量杀害父亲,或是抵抗男性集团,ta 对他们最大的冒犯和挑衅是在消防车上重新施展女性气质的舞蹈。

《钛》
但最终投身男性集团的她,始终无法回避女性身体的生育命运,绷带缠绕乳房与孕肚,隐喻跨性别必须经历的身体改造过程,传达了感官上的身体痛觉。在成为 Adrian 的过程中, Alexia 披上了儿子这一身份,逐渐获得了从前没有的家庭模式下的情感结构,尽管生理上并没有跨越,但在社会和情感关系上却成为文森特事实上的儿子,这呈现的是“性别关系的全部并不由先天生理所决定”。因为异性恋主导的性别秩序是一整套社会的、家庭的、个人与个人之间的,以及个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的全部逻辑。
《钛》所形成的寓言是,当我们厌弃无法摆脱的、由身份带来的诸多限制,就只能转身投入新的主体想象——比如一个赛博格的身份。在这个新的主体想象中,抛弃了古老的二元性别的所有规定,以此展开了新的乌托邦实践。

《钛》
但电影也提醒我们,这样的乌托邦想象有着现实实践上的空想性,毕竟,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出同一生理性别下的,不同性别表达和情感模式。最终这个生成的新主体,不管是赛博格的机械身体也好,还是酷儿的、模糊二元边界的身体也好,还是会被现实结构所捕捉,难以继续突围。赛博格“出走的决心”,到头来只能付之一炬。
这像极了现实中性少数或是女性的出走之路,我们逃向一个未来,奔向一个远方,但永远只能选择对照着现存结构进行突围,最终这样的乌托邦所打开的可能性空间是狭小的。
无论如何,身体恐怖类型在今天的复兴与盛行或许反衬出一个事实,当外在结构难以被撼动的时候,我们对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的想象,是不是只能通过向内地改造自己的身体入手?

参考文献:
[1] Haraway, Donna Jcanne (1991). Simians, Cyborgs, and Women: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c. Simians, Cyborgs, & Women: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, 119.
[2] [英] 劳拉·穆尔维. 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 [J]. 银幕, 1975(3).
[3] [美] 苏珊·桑塔格. 反对阐释 [M]. 程巍, 译.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21: 6.
[4] [美] 戴维尔·斯卡尔.魔鬼秀:恐怖电影文化史[M].吴杰译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5.
[5] [美] 克里斯蒂安·麦茨等著.凝视的快感:电影文本的精神分析[M].吴琼编,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5.
[6] 包哲寒.“身体恐怖”电影中的女性主义:以朱利亚·迪库诺电影为例[J].探索与批评,2023,(01):145-159.
[7] 李闻思.“女性向”消费的幽灵——好莱坞的伪女性主义逻辑[J].中国图书评论,2022,(01):55-65.
[8] 琳达·威廉姆斯,任慧.电影机体:性别、类型与过度[J].电影艺术,2009,(03):123-129.
[9] 李二仕.酷儿理论与电影[J].当代电影,2009,(06):92-104.
[10] 哈里·M.本肖夫,西恩·格里菲恩,李二仕.什么是酷儿电影史[J].世界电影,2008,(04):4-19.
[11] 徐海龙.德·帕尔玛惊悚片中的性别关系和双重体验[J].当代电影,2008,(01):121-125.
[12] 李闻思.作为表象的女汉子——从邪典电影与女性的关系看“女汉子”[J].中国图书评论,2013,(12):24-28.
[13] 李闻思.“女性向”消费的幽灵——好莱坞的伪女性主义逻辑[J].中国图书评论,2022,(01):55-65.
[14] 李方.好莱坞恐怖电影的“女性威胁”[D].广西师范大学,2008.
[15] 赵奕瑄.恐怖中的邪典形态[D].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, 2022.
[16] 徐悦. 狂热崇拜“邪典”的秘密—邪典电影文化生态研究[D].上海:上海师范大学,2014.
[17] 吴凡. 邪典电影研究[D].福州:福建师范大学,2017.
[18] 王礼迪. 邪典风格—论邪典电影的知觉、故事、观念特征[D].成都:四川师范大学,2017.
[19] 戴锦华.电影批评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4.
[20] 李闻思. 邪典电影:一种亚文化的历史[M]. 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2020.
//作者:李子龙 Lance
//编辑:caicai
//设计:Idril
版权所有,未经许可请勿转载

 支付宝扫一扫
支付宝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
微信扫一扫